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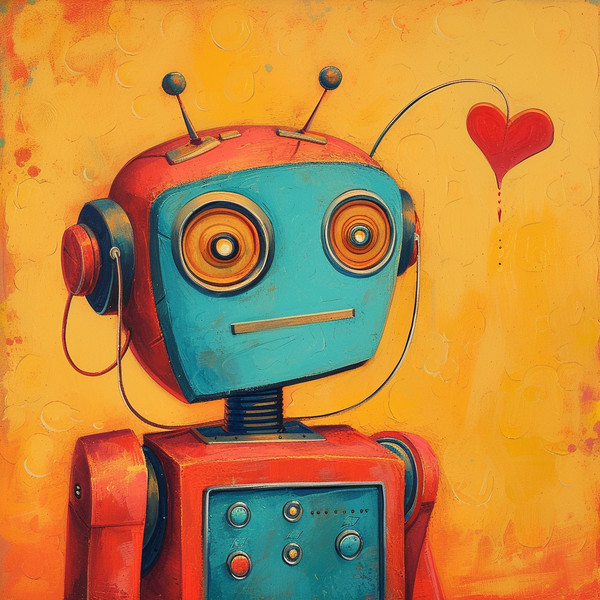
AI搜索削弱网站流量,广告模式崩塌,网络经济陷入危机。
去年年初,Matthew Prince接到了几通不安的电话。来电者是大型媒体公司的高层,他们告诉这位掌控全球约五分之一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Cloudflare负责人,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威胁。Prince最初以为是北韩黑客,但对方回答的只有一个词:“AI。”
从那时起,一个趋势变得愈加清晰: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。越来越多用户不再依赖传统搜索引擎,而是直接向聊天机器人提问,得到的是现成答案,而不是跳转链接。结果就是,曾经依靠流量生存的内容发布者——从新闻网站、在线论坛到维基百科这样的参考站点——流量断崖式下滑。
AI不仅改变了人们浏览网页的习惯,更动摇了互联网赖以生存的经济契约。人类的访问流量一直通过广告变现,如今流量干涸,广告收入枯竭。内容创作者拼命寻找向AI公司收费的新办法,否则,开放网络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完全陌生的形态。
自2022年底ChatGPT上线以来,全球已有约8亿人用它搜索信息。它成为iPhone应用商店下载量最高的产品,甚至让Apple首次承认Safari浏览器的传统搜索量在4月出现下滑——人们把问题交给AI,而不是Google。OpenAI很快还会推出自己的浏览器。
眼看OpenAI和其他后起之秀风头正盛,Google不得不在自己的搜索引擎中加入AI功能来应对。去年,它在部分搜索结果前插入AI生成的“总览”,如今已随处可见。今年5月,又推出了类似聊天机器人的“AI模式”,宣称“让Google替你完成Googling”。
但当Google替用户“Googling”,真正访问信息源网站的人就少了。Similarweb对超过1亿个域名的流量分析显示,全球搜索流量(指人类访问)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下滑了约15%。其中,科学与教育类网站访问量下降10%,参考网站下降15%,健康类网站更是暴跌31%。
对依赖广告或订阅的公司而言,访客减少等于收入锐减。Dotdash Meredith的CEO Neil Vogel感叹:“我们和Google曾经合作愉快……但他们打破了契约。”三年前,该集团旗下网站超过60%的流量来自Google,如今只有三成多。“他们用我们的内容来和我们竞争。”Vogel直言不讳。而自从Google上线AI总览后,新闻搜索结果不再产生后续点击的比例从56%升至69%。
“互联网的本质变了。”Stack Overflow的CEO Prashanth Chandrasekar无奈地说,“AI几乎扼杀了大多数内容网站的流量。”由于访问减少,Stack Overflow的问答板块新提问也越来越少。维基百科也发出警告:AI生成的摘要没有署名来源,正在阻断人们接触和贡献内容的路径。
为了留住流量和资金,大型内容生产商开始与AI公司谈授权协议,同时提起诉讼,用News Corp的CEO Robert Thomson的话来说,就是“又哄又告”。News Corp已经和OpenAI签约,同时旗下两家公司起诉了AI搜索引擎Perplexity。纽约时报一边和Amazon达成协议,一边起诉OpenAI。类似的交易与诉讼此起彼伏。(经济学人集团尚未授权训练模型,但允许Google在某项AI服务中使用精选文章。)
然而,这种策略也有边界。加州法院最近在两起版权案件中判决支持了Meta和Anthropic,认为用他人内容训练AI属于合理使用。Donald Trump更公开支持硅谷的观点,认为要让美国抢在中国之前发展未来科技,他甚至撤换了曾质疑AI训练合法性的版权局负责人。
AI公司更愿意为持续访问信息付费,而不是为训练数据埋单,但目前的交易金额都不算可观。Reddit与Google签署了一年6000万美元的内容授权协议,但今年2月因搜索流量不稳,用户增长低于预期,市值却腰斩。(尽管之后增长回升,股价部分恢复。)
真正棘手的问题是,网络上数以亿计的小网站既无力讨好,也无力起诉科技巨头。它们的内容对AI来说整体重要,但单个网站却可有可无。即使它们想联合谈判,反垄断法也禁止这么做。它们可以屏蔽AI爬虫,但那意味着在搜索结果里彻底隐身。
软件提供商或许能帮点忙。Cloudflare的新客户如今都会被问是否允许AI爬虫抓取内容,以及用途为何。凭借庞大规模,Cloudflare比多数公司更有机会推动一种“按次付费”模式,让网站向爬虫收取“入场费”。“我们必须制定游戏规则。”Prince说,他理想中的结果是“人类免费获取内容,机器人付出高昂代价”。
另一种方案来自Tollbit,它号称是“给机器人设的付费墙”。网站可以按内容价值向AI爬虫收费,比如新文章比旧文章贵。今年一季度,Tollbit为2000家内容生产商处理了1500万次微支付,合作方包括美联社和Newsweek。Tollbit的CEO Toshit Panigrahi指出,传统搜索鼓励千篇一律的内容(如“超级碗什么时候开始”),但收费模式则激励独特内容。收费最高的居然是一家地方报纸。
还有ProRata,由Bill Gross创办——这位90年代就开创了点击付费广告的人,如今提出:把AI生成答案旁边的广告收益,按内容贡献比例分给原网站。ProRata运营自己的AI引擎Gist.ai,已与包括金融时报和大西洋月刊在内的500多家合作伙伴共享广告收入。虽然目前还不足以威胁Google,Gross坦言目标是“树立一个公平的商业模式,让别人最终效仿”。
内容生产者也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。Stack Overflow的Chandrasekar说,“互联网的未来不再只依赖流量”,它已转向企业订阅产品Stack Internal。新闻出版商也在为“Google零流量”做准备,靠邮件简报、应用直达用户,或把内容放在付费墙后,甚至转向线下活动。Dotdash Meredith称尽管Google带来的访问减少,但整体流量仍在增长。音视频内容也因法律和技术原因,比文本更难被AI概括,目前AI回答最常跳转的站点其实是YouTube。
并非所有人都认同“网络在衰亡”。Google的Robby Stein反而认为“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时刻”。AI让内容生产更容易,网站数量两年内增长了45%。AI搜索让人们能用全新方式提问,比如拍下书架照片请AI推荐下一本书,这可能带来更多访问。AI查询可能扫描数百个页面,引用比人类更广泛的来源。
至于Google是否真的减少了向网站导流,Stein称没看到显著下降,但拒绝公开具体数字。他还提醒,人们访问网站减少可能是因为刷社交媒体或听播客。
互联网的“死亡”其实已被预测过多次——先是社交网络,再是手机应用,但最终都没有真的终结它。不过,AI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。如果网络要维持接近现有的形态,网站必须找到新的付费模式。Gross直言:“人们无疑更喜欢AI搜索。要让互联网存活,让民主存活,让内容创作者存活,AI搜索必须与创作者分享收益。”
本文译自 Economist,由 BALI 编辑发布。
仁信配资-宁波股票配资网-按天配资交易-港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